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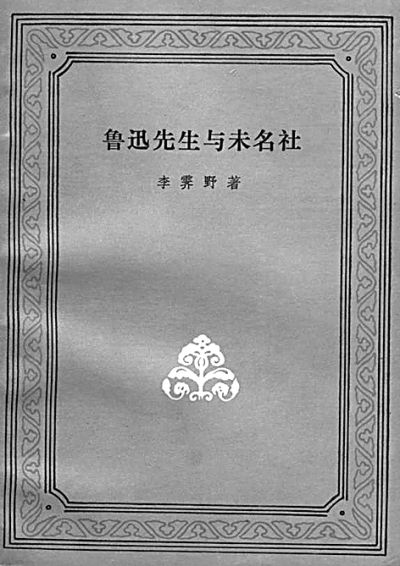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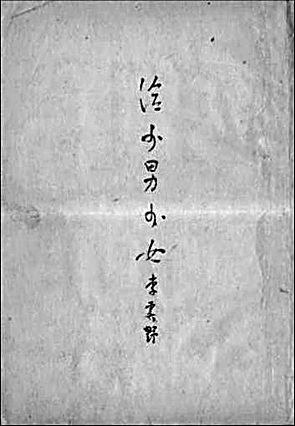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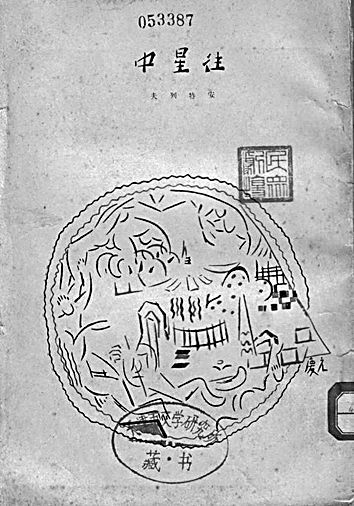
【述往】
1984年,為紀念我的父親李霽野先生從事文學活動60周年,天津文聯特地舉行了一次座談會,經父親本人過目同意,時任中國作協黨組成員、書記處常務書記的鮑昌對他做出這樣評價:五四運動鍛煉出來的文藝戰士,魯迅的忠實弟子和魯迅的研究家、宣傳家,充滿革命激情的作家與詩人,文學翻譯園地的辛勞園丁,不斷追求光明進步的革命者。而作為后輩,回顧父親的全部文學生涯,我覺得大體上可以用三個“始終不渝”來概括。
筆耕
一是筆耕始終不渝。
父親寫詩著文,留下了《影》《溫暖集》《馬前集》《給少男少女》《意大利訪問記》《懷舊集》《我的生活歷程》等小說、散文,《鄉愁集》《露晞集》《國瑞集》《卿雲集》《琴與劍》等古體和現代體詩集和兩部敘事長詩《海河岸上人家》《史灣趙平》,以及兩部詩詞啟蒙。他晚年還曾設想選編中國古典抒情詩。
1984年,天津市文聯為父親祝賀從事文學活動60周年,是從他1924年翻譯完《往星中》算起的,但實際情況是,1919年他就與同學合辦了《新淮潮》。如果以這時為起點,到他1993年編注的《唐宋詞啟蒙》問世,持續時間就是65年。
父親的這種堅持,完全源於他對文學的喜好和出於適應時代的需要,絲毫沒有追求功名的因素。
如果說,《馬前集》是遵循了魯迅先生關於“遵命文學”的教誨行事的話,那麼,寫下《溫暖集》《懷舊集》中的篇篇文字則是父親寄托了自己對親朋好友的思念。
如果說,《國瑞集》展現的是一個從舊中國走來的知識分子對欣欣向榮的新中國的良好祝願與期望的話,那麼,《鄉愁集》則是真切記錄了抗戰期間骨肉分離的苦楚和對重聚的憧憬。這些都與時代脈搏合拍。
正因為如此,當這些深切真實的感受在“文革”中受到惡意歪曲和污蔑時,父親才會全然不顧可能會遭遇的風險,進行了頑強抗爭。他伏案疾書,在被“流放”的“寒舍”裡,趴在不到半米見方的床頭櫃上,一字一句地抄錄下《鄉愁集》和《國瑞集》中的全部詩文,並附上抗戰時期寫有這些詩文的家信和蓋有郵戳的信封。
父親在抗戰年代的六篇演講,本是為解決當時條件艱苦、學生無書可讀的困境所作,僅僅列了提綱就上台侃侃而談了,為的是讓學生“解渴”。而六篇演講總共4萬多字,並無出版打算,只是事后才根據學生留下的記錄,整理成為演講集《給少男少女》。
不曾想,《給少男少女》后來流傳甚廣,甚至是在網絡盛行后不斷被網民轉抄,而且在父親離世近20年后還被再度出版,對青年如何看待人生和讀書仍能有所啟迪。
“多一點知識,就容易多一點愉快的經驗,也就是生活廣一點”﹔“從以前的人手中接過火炬,再將它傳給后來者。使火炬不熄滅,或更進一步增加它的光,便是人生的意義和價值”﹔“人生確是無常的,不過人生的可愛處也多半就在這無常”﹔“慣壞的孩子還不如早死了父母”﹔“小孩子有他們自己的人格,自己的生活,母親的責任是要教養他們慢慢獨立起來,不應使他們總成為自己的附屬物”﹔“世間最美的東西往往是最脆弱的,例如花。愛是嫩美的花,需要小心的培植。所以除了知識之外,愛的藝術需要入微的體貼。不澆水,花是要枯死的。沒有體貼入微的培植,愛也要枯死”﹔“在明了愛的藝術的人,結婚不是愛情的終結,卻是愛情的延續”﹔“我們和十個人相交,未必有兩三位可以成為朋友﹔從書中所得到的友誼溫情,比例卻比較高”等等,《給少男少女》中的這些隻言片語,都曾被一些讀者節選,作為指導自己生活的警句。
深情
二是懷念魯迅先生的深情始終不渝。
自1936年11月魯迅先生去世后寫下《憶魯迅先生》一文起,到1993年9月寫下最后一篇憶文《在魯迅家吃炸醬面》,父親幾乎每年撰文,留下了結集出版的《紀念魯迅先生》《魯迅先生與未名社》《華誕集》等,如此堅持了近60年。
談到父親與魯迅先生的關系,就不得不提及父親的摯友李何林伯伯。他們都非常崇敬魯迅先生,但表現形式卻有很大不同。李伯伯注重學術研究,傾心於此項事業,是公認的魯迅研究權威專家﹔父親則是更多地把自己同魯迅先生接觸的種種親身經歷和點滴體驗記錄下來,給后人以啟示。
雖然有關魯迅先生的著作以及就魯迅研究和各方人士的通信,在父親的文集中佔有重要位置,但是他一直不大同意別人稱其為“魯迅研究專家”。近60年來,父親從來都是以魯迅學生的身份來懷念這位導師的,並一直致力於弘揚這位文學巨匠的偉大精神。
李伯伯認為,父親的《憶魯迅先生》和晚年寫就的《魯迅先生與未名社》是“敘述魯迅先生與未名社的少有的書”。后者則被魯迅研究專家陳漱渝先生稱之為“霽野師的親見、親聞、親歷,為研究中國現代社團史和文學史者所必讀”。
在父親與魯迅先生的交往中,分量最重的部分要算是未名社的這段經歷了,雖說前后隻有6年左右時間,卻不僅是父親終生難忘的歲月,而且是他堅持走完自己漫長的文學道路的重要動力源泉。
未名社創辦之初,父親還在燕京大學讀書,韋素園病倒,他不得不放棄繼續學習和報考研究生的機會,挑起支撐未名社的重擔。李何林伯伯對這段經歷做了這樣概括:“未名社成立后六七年間的編輯、印刷、出版、發行等大量工作,在魯迅先生領導下,除開始半年由韋素園主持,最后一年左右由韋叢蕪負責外,其余全由他無償地負責並擔當一切風險,出版了二十幾種書刊和堅持編印了六年左右的半月刊(《莽原》共48期,《未名》共24期),是很不容易的,而且始終維持著魯迅先生定下的進步方向,更不容易。”
上海魯迅紀念館前館長王錫榮先生則在紀念我父親誕辰110周年時做出了這樣總結:“李霽野先生與未名社的關系,可以用幾個與‘六’這個數字有關的數字來說明:未名社的成員總共是六名,它的存在時間是六年,而在未名社結束之后,李霽野先生又生活了六十六年。在這六十六年的歲月中,李霽野先生始終懷著一種深沉的魯迅情結,也可以說是‘未名社情結’。也就是說,為了這六年,他背了整整六十六年的精神十字架。”
我的母親則更生動地記錄了她的丈夫在回憶起那些終生難忘又飽含辛酸的往事時的心境。她在《伉儷生活五十年》一文中寫道:“(李霽野)也曾深嘗過朋友生疏的痛苦,我看見他在寫《魯迅先生與未名社》的時候,有時伏案啜泣。我勸慰他,他隻引用了勃朗蒂(勃朗特)的一句話:但願這隻‘是由於我們太高評價了他們對我們的喜愛程度和意見’。”
如果了解父親寫下這些紀念文章時經歷的感情波折,恐怕就不會有人輕薄地對他的這些文字做出無端指責了。
翻譯
三是從事翻譯始終不渝。
自1923年編譯短文起,到20世紀80年代重新校改譯稿和有意再著手翻譯一些英國隨筆,父親又是持續了60余年。他先后翻譯了《上古的人》《簡·愛》《魯拜集》《四季隨筆》《戰爭與和平》《被侮辱與損害的》《虎皮武士》《難忘的一九一九》《在斯大林格勒戰壕中》等多國名著,結集出版了英國抒情詩集《妙意曲》、蘇聯及東歐國家作家的《不幸的一群》、蘇聯作家的《衛國英雄故事集》和《山靈湖》、英美國家的《鳥與獸》和《萊比和他的朋友》等短篇小說集以及托洛茨基的論文集《文學與革命》。
在這些眾多譯作中,除父親特別偏好與他心境相投的《四季隨筆》外,特別值得說說的是兩部長篇小說。
一部是夏洛蒂·勃朗特的《簡·愛》。茅盾先生曾寫《〈簡愛〉的兩個譯本——對於翻譯方法的研究》一文,對同一年問世的伍光建譯本和李霽野譯本做出了中肯的評議,他認為,“對於一般讀者,伍譯勝於李譯﹔但對於想看到些描寫技巧的‘文藝學徒’,則李譯比伍譯有用些罷”,並特別贊許了李譯的“謹慎細膩和流利”,在一些段落裡,讓讀者“在‘知道’而外,又有‘感覺’”。
讓后人更加欣慰的是,茅盾先生評論的這兩位《簡·愛》譯者之間並無“文人相輕”的俗氣,而是“十分尊重別人的成就,衷心地欣喜於這樣的成就”。
父親的這個《簡·愛》譯本幾經再版,一直到“文革”期間都還有不少喜愛它的讀者。“文革”后又出現了各種譯本不下二十余種,父親的譯本不可避免地成為翻譯和研究各種《簡·愛》中譯版本的一個“靶子”,他所採用的直譯法也成為這些研究中經常涉及的話題。
正如翻譯界普遍認為的那樣,父親繼承了魯迅先生主張直譯的傳統。其實,在翻譯實踐中,他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直譯法觀”,隻不過並未作過太多的理論研究。1981年4月,他在《悼念茅盾同志》一文中就曾表示,“字對字的直譯容易變為死譯,是不可取的。我的譯文有時就有這樣毛病。”
1983年6月,父親在給南開大學外文系一位畢業生的信裡明確表示:“我主張直譯,隻要中文能合規范,看得懂,要盡量保存原文語言風格特色。這點難做好,但要努力。譯文晦澀難讀,不能算直譯,只是死譯。好的直譯能本身成為好文章,與意譯並無矛盾,改動太多的所謂意譯,與硬譯同樣不可取。形容詞過多是一困難,可以用簡練的中文達意,不一定逐個照搬。句子太復雜太長,可以適當化為簡短。接聯詞太多,有時在中文無必要,可略。”
1985年底,在天津翻譯工作者協會成立大會上致詞時,父親又把這種看法精煉地概括為“精心移植,盡量保存原著的文字美,思想美,風格美”。
在各種不同版本《簡·愛》中譯本開始出現的初期,也曾有出版社找到父親詢問出版其譯本的可能性,並提出應該改用現在流行的風格。
父親沒有同意。
直到1982年,父親才在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經過再次校改的新版本。從表面上看,這是因為他對風格的改變不能苟同,但更深的意義,還是包含在他在新譯文扉頁上加上了“敬以拙作紀念魯迅先生百年誕辰”這十四個字裡。這凸顯了父親對早已故去的魯迅先生的無限哀思。
為什麼這樣說?那是因為大概在1933年秋,父親考慮並准備翻譯《簡·愛》。在開始翻譯后,他接到馮雪峰的來信,轉達了魯迅先生的談話,說未名社既已結束,父親做了教授,就不再努力翻書了。
魯迅先生表達的這種不滿讓父親感到慚愧不安,由於不願因未名社出現的麻煩而干擾魯迅先生,他隻能把這種煩惱壓在自己心裡。整整一年八個月,他都沒有給魯迅先生寫信。
在得到馮雪峰轉告的話后,父親得知魯迅先生還在這樣惦念著他,於是立即寫信告訴了魯迅先生,“我正在翻譯一部長篇小說”。
這裡說的“一部長篇小說”就是《簡·愛》。
但從我現在接觸到的材料來看,沒有足夠的証據說明魯迅先生見到了出版的《簡·愛》單行本。據父親自己的回憶,1936年,他最后一次在上海拜見魯迅先生時是否提及此事,也不得而知。所以,恐怕可以說,翻譯這部小說是父親落實魯迅先生對他期望的一個實証,但遺憾的是,魯迅先生生前未能見到這部譯著。這可能也是父親要扉頁上加上那十四個字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一種對自己導師姍姍來遲的交代。
在《簡·愛》出版后,最能証明父親始終不渝地沿著魯迅指引的道路前行的,就是他著手翻譯列夫·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這更大部頭的名著。翻譯用去了他4年半的時間,完稿時又恰逢魯迅先生逝世五周年,這也是他十分在意的。
父親的想法是,“如能譯完出版,對抗日戰爭也能貢獻一點力量”。我做過一些考察,如果他的譯作能夠出版,至少又可以成為最早的中文全譯本之一,但可惜的是,由於日寇作梗,書稿被毀。四年半的辛勞毀於一旦,這對一個熱衷於文字工作的人來說,該是多大的打擊呀!
但父親只是心平氣和地說,在戰爭中損失的生命財產多著了,這不過是滄海一粟。從他個人說,譯文是從英文譯的,恐怕質量也不佳,不印成倒是好事。這樣偉大的著作,將來會有人從原文直譯的。此后,他又寫作和翻譯了許多作品,並沒有因此而氣餒。
淡泊
父親的勞動成果被毀不止這一次。他在抗戰時期翻譯的《俄默絕句集》(即《魯拜集》)和在1961年寫成的2000行長詩《史灣趙平》被毀,就是“文革”中發生的兩個例子。前者因老友朱肇洛先生曾轉抄而留下了副本,才得以收入文集,與讀者見面。后者就沒有那麼幸運了,留下的隻有曾在雜志上發表過的兩個片段,收入《李霽野文集補遺》之中。這部長詩是他在80歲時才根據記憶重寫出來的。正如父親自己在長詩后記裡所說:“我自己知道這算不了詩,只是奉獻萬千先烈的虔誠薄奠罷了。”
我想,在這件事上,父親想到的完全是留住對一位自己熟悉烈士的記憶,正如文章開頭所說的那樣,他絲毫沒有追求功名的因素。其實這是他時常保持的一種心態,在其他許多地方也都可以看得出來。
父親是天津設立魯迅文學獎的倡導者,但他卻一再謝絕授予此獎,“對魯迅先生,我是尊敬的,對用他的名字設立的獎金我自然以能配得到為榮﹔但若覺受之有愧,那就於心難安了。”最終經過幾番勸說,他才在90誕辰時接受下來,並立即作為以他命名的助學基金,贈給了南開大學。
父親是自魯迅先生提議成立的未名社以來的長期主要負責人,卻斷然拒絕被稱為“未名四杰”之一,隻願被稱作“未名社成員”。抗戰期間,他每月都要從自己微薄的薪金裡抽出一部分,接濟魯迅先生家中幾乎斷炊的兩位老人 。
新中國成立后,在自己尚需承擔大家庭生活開支的情況下,父親還每月拿出錢來幫助一位因經濟困難想要退學的學生,而他從來都不對別人提起這些事。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在“文革”中受到審查、批判時,他曾寫過一份有關自己歷史的正面材料,詳細列舉了他在新中國成立前幫助過的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
我曾做過統計,在父親公開發表的文章裡、在別人寫他的文章裡,以及在別人的傳記中,不同程度地提到過他幫助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的事,涉及的人加在一起,不及他在那份材料裡說的多。更何況有些當事人在自己的文字裡提到過父親的幫助,而他自己卻忘卻了。
我作為后代,也是在父親離世十多年后,因為要紀念他誕辰110周年,才看到了這份文字。他把自己所做的一切都看成是平常的分內之事。
沉默不等於忘卻。默默懷念父親是我一直堅持的做法。雖然,在父親去世后的這些年裡,不斷有人著文懷念,他的作品也不斷被收入各種文集,這說明人們還沒有忘記他。我也只是希望,隨著時光流逝,李霽野,這個名字能和千千萬萬曾作出過大小不同貢獻的人們名字一道,漸漸融入歷史的長河。
李方仲,李霽野先生之子,1940年生於北京,1964年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學院俄語系,后在中共中央辦公廳、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工作,曾任我駐蘇聯、俄羅斯使館參贊。
(本版圖片均為資料圖片)
學人小傳
李霽野,1904年4月6日出生於安徽省霍邱縣葉集,入私塾附讀,在明強小學、阜陽第三師范學校讀書,因贊成新文化,傾向共產主義思潮而受排擠退學。1922年與韋叢蕪合編《微光周刊》《微光副刊》。1923年入京,上崇光中學並發表譯文。1924年譯完《往星中》,往竭魯迅先生,加入先生建議成立的未名社,堅持六年,編印半月刊(《莽原》共48期,《未名》共24期),曾因出版《文學與革命》被捕。1930年任天津河北女子師范學院英語系教授兼主任,譯《簡·愛》,於1935年出版,以稿酬作川資赴英旅游。次年4月回國后赴上海訪魯迅先生,隨后開始譯《戰爭與和平》,用時4年半,文稿后被日寇所毀。1938年秋到北平輔仁大學教課。因日寇憲兵注意其行動,1943年初逃出敵陷區,先后在復旦大學、白沙女子師范學院任教。1946年9月應許壽裳約,到台灣省編譯館任編纂。1949年4月返回天津,到南開大學外語系任教,1950年任天津文聯副主席,1951年—1982年任南開大學外文系主任。“文革”前曾任天津文化局副局長、局長。1982年被選為天津文聯主席。1996年12月被選為中國作家協會名譽副主席。1997年5月4日在天津寓所逝世,享年94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