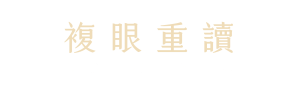

作者 | 羅頌恩(東海大學美術系講師)
改編自 | 2023年11月8日輔仁大學宗教學系演講「基督教藝術的心像世界──睜開眼的祈禱」
楔子
在今日多元文化框架中談論基督教藝術的前提,首先需確立認知的範疇是在視覺藝術發展的脈絡之中,以此區別基督宗教在音樂、戲劇和多媒體展演的其他形式特質。其次是對應「當代藝術發展」的時代屬性,將藝術特質溯源於宗教改革的文藝復興時期的現代性,以便能夠脫離將藝術視為美的同義複詞的「真善美」古典原則。
與過去相比,十六世紀的視覺藝術發展已脫離傳統認知的「機械藝術」(artes mechanicae/手工藝術),轉型成為強調思想與寓意表達的「自由藝術」(artes liberales)。到了十七世紀荷蘭繪畫的藝術自由市場及法國藝術學院的沙龍展覽模式越趨盛行的年代,傳統依存於教堂空間或權力機構的藝術委託現象也逐漸式微,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強調個人化表現的現代性創造。
然而,在連續性的時代脈絡中,屬於新時代的「現代藝術概念」一直都帶有中世紀宗教文化的存在特質,就是早期作品產生時,都因為「依存教堂空間」而有的「歸屬感」,以及因宗教儀式需求產生的「神聖敬畏感」。
在這個條件下理解十九世紀後期和二十世紀初期的藝術表現,可以看到在脫離正統典範的現代化思潮中,大量出現了個人風格化與主義宣言的藝術詮釋現象[1]。例如塞尚(Paul Cézanne, 1839-1906)在寫給象徵主義畫家Emile Bernard(1868-1941)的書信內容,便展示了新時代創作者的作品詮釋不再迎合過去的美學認知:
羅浮宮是一部書,我們在其中學習閱讀。然而,我們並不能滿足於維持前人已經創造出的美麗公式。讓我們前去研究美麗的大自然,讓我們試著解放我們的心靈,讓我們按著個人的性情來表現自我。[2]。
或者在「藝術自主」的創造追求上否定了相同主題的傳統定義。如超現實主義畫家恩斯特(Max Ernst, 1891-1976)的畫作《聖母在三位見證者面前教訓幼年耶穌》(1926/01)一樣,以體罰管教的圖像取代神聖崇敬的原初含義,強化了現代基督想像深具啟蒙教養文化的時代框架。我們可以將這些現代性的表現視為一種「基督教藝術」確實脫離了教會委託傳統之後的自主性發展。它是文藝復興「思想性創造」與神聖獨一性的個人化延續,也是教堂藝術世俗化後的「歸屬感」表現。

這對重視主題與形式一致化的基督教藝術來說是一項重大的挑戰。因為在藝術現代化的趨勢中,基督宗教主題的作品價值與魅力已全然讓位給「藝術自主性」的創作者。在他們的詮釋下,這類型的現代藝術吸引了藝術愛好者藉此追求一種深刻的精神生活,但少有人會因此再走向基督宗教的世界去了解其教義內涵與信仰深意。
換句話說,即使是關於基督教相關畫題的表達,現代的創作者與觀眾群都已經可以不再經由基督教會而自行在觀照與想像中獲得內在體會的滿足感。那麼,對基督教與天主教的社會參與來說,是否就只能從自由的現代藝術世界中退出,藏身在與狹義的宗教藝術範疇之中?或者是面臨了什麼樣必須解決的課題?以重新獲得與現代世界共存的有效基礎?
本文的寫作內容是筆者於2023年11月在輔仁大學宗教學系演講的後續整理。在重新調整結構過後,將從基督教藝術現代化發展的歷史脈絡出發,進一步說明此範疇中基督教與天主教的現代化藝術路徑與課題,並藉由《羅斯科教堂》回應天主教的藝術現代化改革成果,以及基督(新)教能夠再次參與「現代藝術」的藝術實踐之可能。
基督教藝術生成的歷史時代及其特質
在九世紀卡洛琳王朝文藝復興(Carolingian Renaissance)期間,以及十一世紀開始的十字軍東征現象裡,教堂建築與聖地朝聖文化逐漸讓「視覺」成為基督宗教重要的信仰實踐之依據。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教堂空間收藏的大量聖骸之物具體化了象徵「上帝居所」的教堂所擁有的神聖外顯形象。於此連帶地賦予了出現在教堂空間裡的視覺創造,如主教權杖、大禮袍、聖餐禮之器皿、詩班服、雕塑、壁畫等可視之物,在崇拜儀式的整體氛圍中染上了一層神聖展現的色彩。因此,對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宗教傳統來說,在中世紀「聖像破壞之爭」(Iconoclasm, 8th- 9th C.)過後,教堂圖像的存在已是合法且具有神聖的本性。
按這樣的前提進入朝聖文化的範疇,將會發現藝術畫作或雕刻的存在除了是一種信仰寓意或神學意涵的可見指涉之外,對朝聖者而言,也是他們實踐虔信生活與追求赦免的重要目標和確據。對帶著罪性意識前來藝術作品面前參與聖禮的朝聖者來說,這種具有神聖屬性的藝術觀看就是一種具有贖罪證明的虔信實踐。換句話說,中世紀末期到十六世紀宗教改革白熱化之前,對教堂裡的藝術作品進行神聖觀看的心理反應,有很大程度呼應了啟蒙精神的現代人的內觀式個人意識。
以大英圖書館收藏的羊皮卷插圖「虔誠靈魂的三個靈修狀態」(Tres etaz de bones ames, c. 1300/02)為例,畫中默觀的修女操練著個人內在的三個靈命階段。而讀畫的靈修者也在視覺的觀想中同步意識到個人的(宗教性)自省與自覺。

靈修的第一階段由左方上下圖畫顯示,是人參與「吿解」與「領受聖餐」(聖血)。在這個外顯的宗教儀式活動裡,人以「屈身跪拜」的自我懺悔作為預備,在心中經歷敬畏而開始走向「與神聖相遇」的靈命操練。
靈修的第二階段在右上圖的引導下進入「內在觀想」。在注目以「基督加冕馬利亞」為主題的祭壇雕塑中(不論畫中修女或者觀圖的信仰者都是相同的自覺狀態),虔信的跪立姿勢連結了修女與尊榮聖母內心順服於基督的性情。對觀畫者來說,只有在清醒的自覺之中才能明白圖像類比的意義,是要人看見效法神聖榜樣是基督所喜悅的信仰美德。在第三個階段中,信仰者以展開雙手跪求祈禱的態度觀想「釘十架的基督」,以領受祂所展現的「三一神」的啟示之愛,以及自己赦罪後的新生命得以與「合一的神」合一。
又或是《聖血祭壇木雕圖》(Heilig-Blut-Altarm 1501-1505/03)的主祭壇圖所顯示的,在圖像形式的引導中凸顯了觀者對自我內在的省思意識。雕刻家里門施奈德(Tilman Riemenschneider, 1460-1531)為Rothenburg的聖雅各大教堂製作了一件大型的祭壇雕塑,以便能夠常態性地展示十三世紀因聖餐儀式意外濺灑出來的「聖血」[3],讓「西班牙聖雅各之路」的信徒得以在路徑中前來朝聖,領受它已負盛名「使人得醫治」的神蹟奇事。

祭壇的主畫面對應的主題便是「最後晚餐」,但浮雕構圖的中央主角並非是敘述事件中的人子耶穌,而是那晚出賣主的猶大。他在祭壇垂直的主軸線結構上對應著上方鑲嵌的「聖血」,以及下方基座處為世人的罪而死的十架基督。
在作品展現桌子外側中央的出賣者「猶大」的做法上,突出走動的身形直接出現在朝聖者面前,勾勒出凝視作品時,觀想得以聚焦於罪性意識的人性課題。因為當時許多特意前來聖物祭壇前的人,有許多是被法院判決確定之後才踏上朝聖之路的有罪之人[4],或者是渴望靈魂得救的虔信者。由於他們渴望著縮短靈魂在煉獄受折磨的時間,心態上自然會有明顯的罪性意識。而這座祭壇雕刻所呈現的藝術形式,讓朝聖者在察覺自己與「走向基督」的猶大相互重疊時,能夠憶起聖經敘事中指出的——罪是「撒旦入了心」(約翰13:2),而更加突出赦罪需要聖血入口的神聖意義。
在基督教世界的救贖文化語境中,視覺藝術作品的存在意義與人內在生命之間有極為深刻的聯繫關係,並引導人在外在世界中具體移動到特定的神聖場域,在觀看圖畫的過程中進入特定的神聖脈絡,或者是法國歷史學家Évelyne Patlagean所定義的「意象天地的領域」(le domaine de l´imaginaire),一種表象引起的寓意體會[5]。這種具有內在指向、歸屬性質與觀看心理反應生成的圖像創造,便是宗教改革來臨之前主要的文藝復興藝術理解。
宗教改革之後的基督教藝術
在宗教改革期間,歐洲基督教文化因為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等人與舊時代政教合一的宗教觀在神學、政治與經濟議題上的分歧與劇烈的辯證過程,造成了神聖的教堂藝術產生了三種主要的發展路線。
首先是在激進的改革宗世界裡對視覺藝術的否定。如Wittenberg大學神學院院長卡爾施塔特(Andreas Karlstadt, 1486-1541)在辯論傳單〈拿掉圖像〉(Von abtuhung der Bylder, 1522)中寫到:「能夠贏得尊敬的,唯獨神。」甚至認為人們在教堂裡向「聖像」屈膝的虔敬行為,都算是對神的褻瀆。這種依照摩西律法禁止雕刻與崇拜偶像的激進態度,拒絕了以羅馬教廷為首的中世紀朝聖文化傳統,也就是否定了具象的視覺藝術存在於教堂中的價值。
從藝術發展的角度來看,卡爾施塔特、慈運理(Huldrych Zwingli)到第二代宗改家加爾文(Johannes Calvin, 1509-1564)等人對「藝術品」的拒絕與連帶在社會中激起的圖像破壞(Bildersturm)浪潮,其實是將視覺藝術推離了傳統的神聖理解,使其有機會轉移到日常的世俗世界。在沒有崇拜儀式的需求下,圖像創作盛行於十七世紀荷蘭地區的藝術自由市場,其外顯形式變得更加單純、少有神聖指涉的美學特質。例如今日常見的風景畫、花卉類型和靜物題材等賞心悅目的世俗繪畫主題,便是屬於後宗教改革時期新教地區的自主性藝術表達。
改革宗基督教的另外一種去神聖化的圖像創造是源自於馬丁路德對藝術的保留態度。他認為人們在聽講道或思想的過程中不可能不在心裡產生相關聯的圖像(印象)。因此圖像的存在在不可避免的前提下,它們也能成為幫助信仰者把「抽象的」教義牢記在心中的重要器皿[6]。1528年大齋期第一主日的講道中,路德具體表明自己非圖像破壞運動的立場,並視藝術作品為一種「可有可無」的存在[7]。這種將視覺作品對應於記憶與思想信仰文本的觀點,讓圖像創造的作者脫離了原本應當符合聖禮儀式的神聖指涉與美學原則,進而開始在「圖以載道」的特質上關注於視覺形式的多元可能性,以及對特定畫題的個人化詮釋與體會。
在宗教改革過後的藝術發展時代脈絡中,上述兩種新教立場的藝術觀讓圖像創作在脫離依存於教堂的關係後變得更加開放,在去宗教化的藝術需求中產生多樣的題材表現形式。換句話說,這種與教會失去顯性關聯的藝術類型反應了基督新教與視覺藝術在進入巴洛克時期之後暫時斷離的平行關係。
第三個教會藝術發展路線是天主教對視覺創作的肯定態度。羅馬教廷在受到改革宗神學家強烈批判之後,更加確立了「神聖藝術」的傳統發展,並於最後一次天特會議(Tridentinum, 1563)中達成定調。這個藝術原則繼承的是教會看重視覺文化的傳統,以及「天主教會大分裂」(Western Schism, 1378-1417)之後,教廷為了重整信仰威信而興起要將廢墟羅馬建造成新耶路撒冷的聖城意象。
在以「聖城羅馬」為目標導向的城市建設計劃裡,視覺藝術的神聖性展現從十五世紀文藝復興開始就是教會主要看重的特質。因此當天特會議要針對教堂藝術進行討論時,積極的神學家,如義大利波隆納主教帕萊蒂(Gabriele Paleotti, 1522-1597)便藉由論文〈論述圖像的神聖與世俗〉(Discorso intorno alle immagini sacre e profane, 1582)進一步指出教堂藝術的內容是不容出錯的,要避免使人產生怪誕等迷惑的視覺想像。在積極面上,必須製造能夠展現「靈魂建造」[8](edificio delle anime)和「敬拜神」(culto di Dio)的感染效應。
這個按著「真善美」原則的美學神聖化、標準化的藝術趨勢,在崇尚「模仿權威典範」的藝術學院機構發展的脈絡中,從義大利擴散到了路易十四的法國,進而成為啟蒙時期的藝術文化主流。因此,當十九世紀歐洲各地開始出現明顯的現代化發展時,藝術在新舊時代更替之間也產生了一個非典型、非道德取向,更直接回應當代思潮的「現代藝術」。而這個屬於新時代的年輕藝術類型,在當時天主教神聖美學的標準中成了被嚴厲批評與拒絕的作亂份子。
天主教與現代藝術的衝突
1888年教宗Leo XIII發表聖誕節《通諭》批判現代主義化的社會趨勢,認為當時盛行的藝術有太多使人犯罪與墮落的刺激誘惑[9],在不知不覺之中「那些無神論的、不知羞恥的戲劇表演、書籍和雜誌,那些嘲諷品德和美化罪惡的藝術」影響了人的心智,也使原本能夠服務於「高貴的愉悅生活」的藝術「降格變成了感官的工具」。甚至到了二十世紀之後,個人化的抽象藝術「就像是『類宗教媚俗』(der pseudoreligiöse Kitsch)相反面的極端」[10],它牴觸了、拒絕了「信仰群體的構成」(ein Widerspruch zu der Verfassung der Gläubigen)[11]。對看重儀式文化與「神聖藝術」(Ars Sacra)[12]的天主傳統而言,現代性的個人主義化不只不是「美善」的合宜體現,同時也易於擾亂信徒教義性色彩的道德生活。
教廷對「現代藝術」拒絕的理由反映出新一代的創作者開始脫離學院傳統美學的仿效關係,改以追求得以實踐「自由創造」的個人主體價值。如馬內(Manet)的《草地上的午餐》(1863/04)將原本應該出現在史詩、神話主題的「裸女」「錯置」於中產階級日常生活場景裡;或者是後來印象派大量留下筆觸和顏料痕跡的作法,則是否定了學院美學長久以來奠定的「無瑕疵」美感;而不斷描繪日常生活的當代觀看(艾菲爾鐵塔、工廠區、蒙馬特紅燈區、拉法葉百貨公司等當代文化),都是藝術遠離傳統教會、學院和宮廷的委託藝術生態之後的現代自主化展現,也是藝術家獨自設題與形式創造的現代性特質。

這個藝術自主性創造的趨勢得以成為主流的另一個原因,則是在分工的現代化社會中受益於專業領域的開展。如十八世紀的藝評活動和博物館建置、十九世紀國家性的文化政策和中產階級深愛的畫廊機制等藝術生態體系,促使現代性作品能夠存在於一個屬於藝術自主的供需世界中。也因此產生了更加激進的藝術形式與風格,如二十世紀的抽象藝術、形而上藝術、觀念藝術等。甚至造成了一種因為現代性特質而脫離現實的藝術精英化現象。
Peter Bürger以社會存在的角度解釋了現代藝術所看重的「藝術自主」(Die Autonomie der Kunst),認為這是一種「脫離日常生活的脈絡,獨立為一個個可以當作整體加以對待的東西」(Peter Bürger,《前衛藝術理論》,1974)。又或是德裔美國歷史學家 Peter Gay的定義,認為現代藝術的創新與多樣性是一種「不熱衷於政治或學說上的中道」、「走在美學安全界線的最前緣,甚至超越」[13]的冒險精神。他進一步地引用馬蒂斯(Matisse)寫給後期印象派畫家勃納爾(Pierre Bonnard, 1867-1943)的書信,再次說明現代藝術創作者拒絕統一化的獨特性格:「我被一些傳統的元素癱瘓了,他們讓我無法表達自我,讓我無法依自己想要的方式作畫。」[14]
這種今日已經是習以為常的「個性化創作自由」反映的正是「渴望取得絕對自主」,甚至看重個人「內心指引」的現代性創作型態。這讓原本還能在美善理想化的文明社會中發生影響力的基督教信仰,開始退居於藝文世界的邊緣地帶,甚至在現代藝術創造的個人化形式裡出現了反天主教美學的藝術表達。如德國畫家Emil Nolde(1867-1956)的《基督下陰間》(Christus in der Unterwelt, 1911/05)便是以刺眼與對比的色彩、扁平無肢體感的形體造型聚合而成一幅宗教主題畫作。而出現在耶穌兩旁的牧師與修士更是被描繪成不莊重的醜陋模樣。這種深具個人化的圖像詮釋「近乎病態」[15],並且證實了在現代藝術的世界裡,即使是關於基督教文化的主題展現,創作者都已不再需要符合基督信仰的傳統認知與期待。

法國天主教的藝文改革計畫
在教會被現代藝術冷漠的二十世紀初期裡,天主教界出現了一位投身於神職呼召的畫家——道明會的修士Marie-Alain Couturier[16]。二戰期間,他和同樣熱愛藝術的修士Pie-Régamey[17]開始一同積極與現代藝術大師展開對話。1936年,他們共同承接了由Joseph Pichard創立的藝文雜誌《神聖藝術》(L´Art Sacré, 1935-1954),進一步地將現代藝術介紹給當時保守的天主教界,並且促成許多教會方的現代藝術委託。如「Assy高原聖母院」的十七位現代藝術家委託(Notre-Dame de Toute Grâce du Plateau d’Assy)、馬蒂斯的《旺斯小禮拜堂》(Chapelle du Rosaire)和「奧丁庫爾聖心堂」的抽象馬賽克玻璃花窗(Sacré-Cœur in Audincourt)等[18]。
在這項法國天主教的藝文改革計畫背後,其神學基礎源自於藝術家天才論是一類「創造的人」(Homo creature),他會在創造工作中「神秘地參與」神的創造活動[19]。同理,那些深具辯證性和感染力的「現代藝術大師」同樣就是具有繼承神性本質的創造者,甚至在教堂儀式的需求意義上,他們能夠創造出比一般教義性作品更令人印象深刻、更有力量的藝術形式[20]。而這個特殊的存在價值在「作者已死」的現代理論概念之下,已化解了教堂藝術對藝術家個人宗派歸屬要求的現實難題。
維也納大學神學院系統神學教授Kurt Lüthi認為《神聖藝術》所帶出來的現代基督教藝術創建是教會對現、當代藝術的開放態度。且認為在神學觀點上,現代藝術的自主性創造會比傳統宗教繪畫更能得以提供深刻性的基督教主題[21]。而變形的風格或抽象藝術(非形象藝術)的絕對自主性都有助於教會文化重視的「超驗」(Transzendenz)與「沈思」(Kontemplation)持續發揮影響力[22]。這股教堂藝術走向現代世俗文化的「法國天主教藝文改革」路線,也在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1962-1965)中獲得了正面回應,確立了羅馬教廷的眾教會在文化事工上的開放態度與基調。
在天主教藝術現代化改革的發展過程中,受到Couturier影響而對現代藝術充滿熱忱的De Ménil夫婦[23]是這些教堂藝術得以實踐的重要經濟支持。由於Dominique Menil的父親在石油探勘工業中獲得巨大的成功,促使這對從法國移民到美國的藝術贊助者能夠進行各樣型態的藝術作品收藏,甚至建立相關藝術研究典藏與教育機構。位於波士頓聖湯瑪斯大學(St. Thomas University)校區附近的「羅斯科教堂」(Rothko Chapel)正是在他們的贊助之下出現的基督教藝術現代化的成果。
Couturier聖化現代藝術的實踐
1964年De Ménil夫婦委託當時已是美國藝壇相當知名的猶太裔藝術家羅斯科(Mark Rothko)為一座天主教校園「教堂」進行創作。無宗教派別、但因成長經歷而排斥猶太教的羅斯科本人非常看重這次的基督教藝術委託,認為De Ménil夫婦的邀請使他把自己「推展到一個能夠超越自己的境界」[24]。而讓極高自主性的抽象藝術成為教堂空間中最重要的存在,很大的原因是來自於Dominique Menil個人對宗教精神性的高度追求。在Couturier的神學藝術觀影響之下,De Ménil夫人認為藝術是一種靈性的重生,「就像雅各的梯子,藝術把我們帶到更高一層的真實世界,帶到永恆,帶到樂園。藝術是可以觸摸和不可以觸摸的結合;古老的聖符神話——天與地的結合。」[25]
羅斯科在紐約工作室規劃了有自然採光天井的創作環境,並且以象徵永恆的八角形展出空間與基督苦路十四站的概念進行壁畫製作。最終所繪製的十八件暗灰色調巨幅油畫之中有四件候補[26],以因應未來建築完工之後的實際空間氛圍。

源於東正教八角形意涵的「羅斯科教堂」(06)雖說是一間「教堂」,但到了最後階段,建築的內與外並沒有安置任何天主教相關的符號與聖像。嚴格來說,「羅斯科教堂」更像是一座現代建築風格的「藝術教堂」。獻堂禮拜最終是在羅斯科逝世一年後的1971年舉行,其儀式由天主教、猶太教、佛教、回教、希臘正教和基督教共同主持,典禮中演奏了現代作曲家Morton Feldman特別為此創作的作品《羅斯科教堂》(Rothko Chapel, 23 min.)。
這座向不同靈性文化活動開放的「羅斯科教堂」在降低了宗派指涉的作用下,成為了匯集宗教性和靈性追求的藝術性載體。許多慕名而來的人如同中世紀的朝聖者一樣,在藝術朝聖的身體移動中進入了「教堂」,置身於獨特的場域氣氛,經歷了觀想過程所激起的內在感知與感動。他們的留言紀錄回應了此間藝術教堂高度的靈性特質。
芝加哥大學藝術學院的教授James Elkins在「藝術使人感動」的課題中對「羅斯科教堂」的訪客留言進行摘錄。其內容使人看見藝術觀想的經歷反應了深度內在感受與特殊場域之間的直接關係,以及藝術感動和宗教體驗高度重疊、相互共鳴的靈性屬性:
「這真是個重要、美麗的地方,這裡對於我們而言可以說意義深遠,可以徹底治癒我們」、「我未曾在一段時間內沈思過這麼久——而且內心在沉思時也未曾如此平靜過。我幾乎無法抽身離開此地。」、「我們可以再藉著這裡好好舒放身心」、「我感到強烈的、徹底的敵意,令人不寒而慄」、「對於我的視覺與內在而言,這都是一次令人目瞪口呆的經驗」、「我忍不住要離開這個地方,當時我已經熱淚盈框」、「初次造訪,感動到流下悲傷的淚水」、「謝謝你們造就了一個可以讓我盡情哭泣的地方」、「這靜默的氣氛深深刺進了我的心」、「這是一次會讓人感動落淚的宗教經驗」、「眼淚,讓我有一種被擁抱的感覺」。
Elkins認為,在被羅斯科的抽象繪畫包圍之下,不知不覺就進入了長時間的觀畫狀態,而藝術欣賞的愉悅感受也就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人的內心被畫作與教堂空間所營造的特殊情境觸及,使之感受到更為強烈的情緒[27]。在這個藝術觀想的活動中,人被挑起了內在敬畏感受的宗教經驗,甚至賦予了觀者在追求精神生活時更深層的靈性意識。
羅斯科教堂從一開始的「天主教教堂」設定到最後「泛宗教性」的場域定位,可說是具體回應了「天主教的藝文改革」努力搭建的跨領域對話事工,甚至導引出無宗派身份的羅斯科對基督信仰釋出好感與回應,以至於賦予了現代藝術發展史具有基督信仰得以參與其中的接點。因此,對當代教會而言,藝術教堂或教堂藝術所創造的深度感知效應提醒了理性務實類型的信仰者,應當再次看重人在宗教改革之後已多失落的靈性意識[28]與特殊場域氣氛之間的緊密關係,讓現代生活中的藝術朝聖也能夠成為教堂存在的另外一種面向。
然而,雖然「羅斯科教堂」使人重拾靈性感知彌補了現代社會與基督信仰之間的疏離感,但在改革宗的神學教義理路上,「羅斯科教堂」的成功其實是帶來了新的難題。對改革宗信仰傳統而言,廣納宗教性的「教堂」就是一間無法對焦在「講道」上面的建築體;因藝術感召而出現的靈性社群也難以成為同屬基督的信仰團契。
面對上述的宗教性難題,本文的最後段落將以羅斯科教堂的藝術源頭,也就是十九世紀德國浪漫主義畫家所創造的內在風景視域來回應這個「教會藝術」現代化的另一個課題。
基督新教的藝術現代化路線
具有基督教虔信派脈絡的德國浪漫主義畫家佛烈德利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 1774-1840)在1810年柏林藝術學院展覽中提出了一組互相對應的油畫畫作[29]——《海邊修士》與《橡樹林中的修道院》(07-08)。紐約大學藝術史系教授Robert Rosenblum(1927-2006)將其中的《海邊修士》看作是美國抽象繪畫發展系譜的原點[30]。

佛烈德利希以相反於學院美學的形式描繪了《海邊修士》,讓一位渺小的修士站在岸邊望向極簡的灰藍色海景。這種看著幾乎空無一物的視覺觀感,與人們到了羅斯科教堂之後在十四幅灰藍紫調的抽象畫作面前觀看一樣,是一種在特殊場域中激起觀者內在精神性感知的藝術凝視。
對十九世紀年輕一輩的評論家來說,《海邊修士》不符合傳統美學的經典再現原則,而是以畫面空無一物的細膩描繪方式反應出當時時代看重內在感受的浪漫主義思潮。《柏林晚報》主編的克萊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 1777-1811)形容這是一種「眼皮被割掉了」[31],好像是人在畫作前睜開眼睛看見心中的內在風景。
《海邊修士》的空無一物海景之所以能夠激起深度評論,是因為畫家有意識地如此創作。在書信研究、藝評紀錄及畫作修復的報告之中,顯示了海上原本有精細勾勒的三艘象徵希望的帆船及「盈月」[32],但最後展出時都被塗抹遮蓋,留下一片只有雲氣的空無狀態[33]。這個特殊的刪除,反應的是佛烈德利希個人對宗教性的內在追求,以及他在閱讀新教神學家施萊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1768-1834)的《論宗教》(Über die Religion. Reden an die Gebildeten unter ihren Verächtern, 1799)之後,用圖畫回應了書中談到的「宗教性直觀」[34]:
永恆的真實觀看者永遠都是安靜的靈魂,當他們環顧自身周遭時,不是與自己獨處,就是單單面向無限觀看,並對於每一個以自己的方式理解『偉大真道」』的人,由衷地感到欣喜。[35]
宗教性直觀的孤寂氣氛除了與《海邊修士》產生共鳴之外,在另一件作品《橡樹林中的修道院》的死亡主題描繪之中,更是在形式與內涵的表現上有著明顯的呼應。佛烈德利希筆下的死亡是由墓園中的廢墟教堂所勾勒出來。它是作為被啟蒙理性時代淘汰的神聖象徵,但卻在畫中進行著尚未消逝的送葬聖禮。這個隱沒於昏暗中的宗教儀式對比了大時代文明亮光的進步浪潮,它像是一股朝著相反方向看去的引言,要人在默觀、默想中轉向內在,記憶生命關於靈魂歸屬的「絕對依賴感」:
現在我正在繪製一幅大畫,我打算在其中描繪墳墓和未來的祕密。那是只有在信仰中才能看到和理解的事,這將是人類有限的知識上永遠的謎。哥德式教堂的遺跡下是被白雪覆蓋的墓碑和墳丘,周圍環繞著古老橡樹。(⋯⋯)太陽已經下山,暮色中,星星和上弦月的光照在廢墟上。濃霧籠罩著大地,只能看清楚上面的牆垣,愈往下就愈不清楚,造型也更不明確,直到地面是整個消失在迷霧中。橡樹在霧中向上伸展枝椏,但是下面的部分已經完全消失了。[36]

德國詩人科納(Theodor Körner, 1791-1813)也以更加基督宗教的語彙回應《橡樹林中的修道院》的內在世界,寫下了〈佛烈德利希的死亡風景〉(Friedrichs Totenlandschaft, 1810)[37]:
大地在極深的哀傷中緘默
被夜的低聲的鬼魅氣息低語圍繞
聽,這狂風如何在老橡樹中沙沙作響
哀嚎在斷垣殘壁中呼嘯
⋯⋯突然,我聽見甜美的和諧之音
如神的話被音符歌唱
光,如十字上的嫩芽
我的星辰微光在眼中炙熱燃燒因此我明白了每個旋律
恩典的泉源流進了死亡裡
那是我的至好同伴
它們透過墓地拉向永恆的亮光
⋯⋯
文中除了以「哀傷」與「鬼魅氣息」回應圖畫情境之外,科納再透過文字描寫「沙沙作響」(枯枝)、「音符歌唱」(聖詩)與十架上的嫩芽之光(燭光)的彼此對應,將視覺風景轉換為聲音風景,進而提出畫中詩歌情境所寓意的基督信仰內涵——是「恩典泉源」的基督復活勝過了死亡,成為那「永生盼望」。
對基督教藝術現代化的實踐目標來說,《海邊修士》與《橡樹林中的修道院》的共同存在,以及文藝評論、藝術家自述和相呼應的神學信仰觀,都一同為觀者揭開了表象背後的畫意。換句話說,不論是他人對佛烈德利希作品的「詮釋」,或者是畫家自己希望透過文字對作品「再詮釋」,都呈現了個人化的基督教藝術現代化的開放性本質。
與《羅斯科教堂》相比較,《海邊修士》的「空無風景」並沒有像羅斯科的「抽象繪畫」一樣是近乎全然開放的狀態。它在創作者及其時代背景的顯性宗教色彩之中展現出指向性的複合特質——從圖畫出發到連結於文敘和思想脈絡,可說是一種不只單看單一作品,還需在圖文共存的藝術詮釋之中進行的整合性視點,為今日的基督教藝術理解帶來了一種關係式的現代定義。也就是在「教會與現代藝術」的命題之下,進入「策展專業」的現代化基督教藝術創造工作。
總結——以連結教會和現代藝術為目的的實踐創造
對羅馬天主教與德國新教來說,現代藝術時代的來臨都讓雙方教會界做出了極大的調整,改變了原本與世俗現代保持距離的態度。如前文所提的法國天主教藝文改革的教堂藝術委託,或者1961年德國福音派教會(Evangelische Kirche in Deutschland, EKD)與具有「文化神學」傳統的馬堡大學神學系合作,成立「教會建築與當代教會藝術研究中心」(EKD-Institut für Kirchenbau und kirchliche Kunst der Gegenwart),使當代的藝術多元更有系統地被放入「教會空間」的課題中進行學術性的談論。或者1999年德國福音派教會與福音派自由教會(Vereinigung Evangelischer Freikirchen, VEF)合作出版關於「新教信仰與現代文化」的手冊《塑造與評論:關於新教與文化在新時代裡的關係》(Gestaltung und Kritik: Zum Verhältnis von Protestantismus und Kultur im neuen Jahrhundert),欲以官方的立場釐清「現代文化」與教會之間的誤解,並創造出福音事工面對「現代藝術」時的實踐基礎。2002年兩大德國新教團體再次合作專題──《相遇的空間:新教視野下的宗教與文化》(Räume der Begegnung: Religion und Kultur in evangelischer Perspektive),以不同的進路觀點論述自主的現代藝術得以在教堂空間中展演的信仰價值。
「教會與現代藝術」之間的共融發展除了在學術性機構中藉由神學、藝術與文化研究等專業領域的相互交流,進而獲得確切的信仰原則和思想課題之外,德國天主教與基督教教界方面也在所謂的教會日(Kirchentag)中,與藝術界合作舉行專題性的藝術策展。如慕尼黑藝術學院的藝術史教授Wieland Schmied(1929-2014)兩次為天主教教會日舉行現當代藝術特展(1980, 1990)[38];以及宗教改革五百週年德國新教教會在威騰堡、柏林和卡塞爾三座城市中聯合舉行的專題展覽:「路德與前衛」(Luther und die Avantgarde, 2017)等,都是基督教會主動走向現代性當代藝術的積極作為。
與大型專題策展相對的現代藝術參與,是小規模但常態性的教會事工模式。以德國為例,許多參與文化連結的教會開始開放自己的教堂空間,讓屬世的當代創作者能夠在有期限的展覽機制中呈現個人化的藝術創作。如1931年為神學家潘霍華封牧的柏林聖馬太教堂(St. Matthäus-Kirche)因理解自己身處在柏林愛樂、新國家畫廊等高度藝術文化區域裡的特質,進而在1999年正式成立了「聖馬太藝術與文化基金會」(Stiftung St. Matthäus),定期策劃(或審議展覽申請)禮拜空間中的相關展覽與藝文活動,讓超越教條式的「現代藝術」能夠成為激發思想談論的另類教堂藝術。或者是萊比錫的尼可萊教堂(Nikolaikirche)深具城市民主發展歷史的特質,便在入口的前廳空間裡設置了歷史性主題的文件展展區,呈現基督信仰內涵與世俗歷史事件之間不同面向的關聯性,為世俗社會與教會之間搭建起互通往來的橋樑。
這些建置教堂空間具有藝文展覽的型態與「羅斯科教堂」的宗教感受性不同,是在藝術閱讀的思想性中產生與基督信仰的關聯。因此,這兩種互相補充與擴展定義的「現代性教堂藝術」型態,可說是在藝術朝聖的現代性生活模式作用下,為教會帶來了非屬教會團體的文化旅人。
在「藝術與基督信仰」的龐大課題裡,上述的例子都回到了「現代藝術進入教堂」和「教會參與現代藝術與文化」的實踐層面,為我們帶來了超越個體作品認知的基督教藝術現代化理解。這是一種跨領域的詮釋性創造工作,也可以理解成一種「藝術需要翻譯」的概念,是為藝術和基督信仰創造互有交集的歸屬感與內在聯繫。期望這樣的觀點能夠帶來些許的參照價值,進而激發出我們自身富有屬地脈絡意義的現代性基督教藝術。
註腳
[1] 對哲學家Danto來說,如立體派、未來派、達達藝術等藝術團體的「宣言」,是二十世紀前半葉主要的「藝術產品」,也是在他的哲學觀念之下所定義的「意識形態時代」,介於藝術大敘事的形式脈絡歷史上的「模仿時代」之後,「後歷史時代」之前。詳見Arthur Danto,《在藝術終結之後》(台北:麥田,2010)頁58-59, 82-83。
[2] Hugh Honour, John Fleming:《世界藝術史》(台北縣:木馬文化,2001)頁736。
[3] 1270年聖雅各教堂的神父在主持聖餐禮時,不慎將聖杯中的液體濺灑出來在布料上的酒漬。這是1215年第四次拉特朗大公會議過後發生的聖餐禮意外。當時聖血與聖體的「變質說」已被確立。
[4] 中世紀人的犯罪在法院審判過後,重大犯行者除了需支付規定之罰金外,往往會被要求參與贖罪的朝聖旅行,並以獲得相關教堂朝聖證明之物件作為核銷的憑據。實例起參照筆者拙作《睜開眼的祈禱》(台北:宇宙光,2022)頁47-48。
[5] 參見Jacques Le Goff的《中世紀關鍵詞》(台北:貓頭鷹,2019)頁15-16;Évelyne Patlagean, L’histoire de l’imaginaire, dans Jacques Le Goff, dir., La Nouvelle Histoire, Bruxelles, Complexe, 1988, p. 307.
[6] 摘錄自筆者的拙作《睜開眼的祈禱》(台北:宇宙光,2022),相關資料來源請見:Benjamin D. Spira: Lucas Cranach, der Maler Luthers. Der Hofmaler und der Reformator- Bindung, Bilder und Bedeutung, in: Bild und Botschaft. Cranach im Dienst von Hof und Reformation (Kat. Ausst., Heidelberg: Morio Verlag, 2015) p. 56.
[7] 「圖像、聖鐘、彌撒聖袍、教堂裝飾、古燈,以及其他相似的我都保留,誰喜愛想要就讓他擁有。那些從聖經書卷和良善的故事而來的圖像,我認為是可以自由存取的(可有可無的),甚至是有益的。因此,我並不與『圖像破壞』(Bildersturm)同一立場。」詳見Freya Strecker: Bildende Kunst, in: Albrecht Beutel (Hrsg.): Luther Handbuch (Tübingen: Mohr Siebeck Verlag, 2010) p. 244.
[8] Norbert Schneider: Geschichte der Kunsttheorie. Von der Antike bis zum 18. Jahrhundert, (Köln: Böhlau, 2011) p. 239 (Die Bilderlehre der katholischen Kirche nach dem Tridentiner: Gabriele Paletots “Discorso”).
[9] Hans-Eckehard Bahr: Theologische Untersuchung der Kunst, Poiesis, München und Hamburg: Siebenstern Taschenbuch Verlag, 1965, p. 74.
[10] Ibid.
[11] Ibid.
[12] 「神聖藝術」(Ars Sacra)中的「神聖」一詞不能只被看作是「藝術表現」的形容指涉。它在天主教信仰的文化脈絡中,對應的是教堂儀式的具體展現。因此對天主教來說「神聖藝術」顯示出藝術作為具體體現神聖臨在的高階特質。
[13] Peter Gay,《現代主義:異端的誘惑》(立緒:2008)頁19。
[14] 同上,頁22。
[15] 時代的藝術工作者Johannes Sievers將Nolde的畫作視為是一種「重病患者的產物」(das Produkt eines Kranken, eines Schwerkranken)。相關文章請見Paula Schwerdtfeger: “Christus in der Unterwelt” von Emil Nolde(畫作評論,April 2014),法蘭克福Städel美術館官方網站:https://stories.staedelmuseum.de/de/bild-des-monats-christus-in-der-unterwelt-von-emil-nolde。
[16] Marie-Alain Couturier原是法國先知畫派(Nabis)Maurice Denis工作室的學生。參照:Horst Schwebel: Die Kunst und das Christentum: Geschichte eines Konflikts (C.H.Beck: 2002) p. 119-120.
[17] Pie-Régamey(1900-1996)出身於具有新教和藝文背景的家庭,1919年進入索邦大學工讀歷史與地理學位;1926年皈依天主教信仰後任職於羅浮宮會畫部,1929年開始攻讀神學,1932年成為天主教修士。資料參考法國《環球百科全書》網站:https://www.universalis.fr/encyclopedie/raymond-regamey/。
[18] Horst Schwebel: Die Kunst und das Christentum. Geschichte eines Konflikts (München: C.H.Beck, 2002) p. 116-119.
[19] Ibid., p. 120-121.
[20] Ibid..
[21] Kurt Lüthi: Mut zum fraglichen Sein. Wege eines Theologen zu zeitgenössischer Kunst und Literatur, Hora Verlag: 1996, p. 11。
[22] Ibid., p. 11-12.
[23] Dominique de Ménil (Dominique Schlumberger, 1908-1998)在法國長大,在索邦大學學習數學和物理。之後繼承父親在石油探勘世界中獲得的巨大財富。1931年5月9日,她在巴黎與法國貴族,同時也是銀行家的讓‧德‧梅尼爾(Jean (John) de Ménil,1904-1973)結婚;1941年De Ménil夫妻先是逃亡至英,再到美國。
[24] 原話為「你們給我的考驗的重要性,從每一個層面的經驗和意義上來看,遠超過我原先所有的想法。這使我能把自己推展到一個我以為超過我可以達到的境界。」(羅斯科給De Ménil夫婦的信),摘錄自《羅斯科傳》,頁464。
[25]James Breslin著,張心龍、冷步梅譯:《羅斯科傳》(遠流1997)。頁487。
[26] 紐約工作室內部的光線來自於中央天井式的自然採光,與八角形教堂建體設計一樣的型態。在這個條件下,羅斯科的畫作數量從原初規劃的十件增加到最後的十八件。從這裡來看,不論是工作室空間的營造,或者創作數量,都反映出羅斯科對此委託案的重視。
[27] James Elkins:《繪畫與眼淚》,左岸:2004(2000),頁25。
[28] 這裡所提到的「靈性意識」不是無意識的感覺反應,不可與靈媒或降靈會混為一談,而是Rudolf Steiner提出的觀點:「將思考視為一種『屬靈活動』」。說明參照Gerhard Wehr的著作《榮格與史坦納》(心靈工坊:2023)頁106-109、184-186。
[29] 根據柏林舊國家畫廊自2013年進行到2016年的畫作修復報告指出,《海邊修士》與《橡樹林中的修道院》不管在創作時間、材料、技法和風格上,確實是屬於同一時期的藝術創作。參照:Kristina Mösl, Philipp Demandt(Hrsg.) : Der Mönch ist zurück. Die Restaurierung von Caspar David Friedrichs Mönch am Meer und Abtei im Eichwald(研究報告書),出版:Nationalgalerie- Staatliche Museeun zu Berlin(柏林國家美術館群)、Alfred Krupp von Bohlen und Halbach-Stiftung(基金會): 2016.
[30] Robert Rosenblum在1975年出版了專書《現代繪畫與北方浪漫主義的傳統》(Modern Painting and the Northern Romantic Tradition),以作品生成的內在精神和宗教性來取代具像形式變異,嘗試避開形式風格的藝術史觀來建構抽象繪畫的發展脈絡。
[31] 「(⋯⋯)它的單調和無岸感,只有畫框作為前景,所以當人看著它的時候,就好像眼皮被割掉了一樣。儘管如此,這位畫家無疑是在他的藝術領域開闢了一條全新的道路;我深信,在他的腦海裡,一平方英里的邊疆沙灘可以用一棵小蘗灌木來表示,一隻孤獨的烏鴉在上面飛舞,這幅畫應該就會具有真正奧西恩(Ossian)或寇瑟加藤(Kosegarten)式的效果。(⋯⋯)」(〈在佛烈德利希海景畫前的感受〉(Empfindungen vor Friedrichs Seelandschaft, 1810.10.13)參照:Christian Begemann: Brentano und Kleist vor Friedrichs Mönch am Meer Aspekte eines Umbruchs in der Geschichte der Wahrnehmung (Deutsche Vierteljahrsschrift für Literaturwissenschaft und Geistesgeschichte 64, 1990) p. 89-145.
[32] 參照修復研究報告書:Kristina Mösl, Philipp Demandt (Hrsg.) : Der Mönch ist zurück. Die Restaurierung von Caspar David Friedrichs Mönch am Meer und Abtei im Eichwald, 2016.
[33] Herrmann Zschoche (Hrsg.) : Caspar David Friedrich. Die Briefe (Hamburg: ConferencePoint Verlag, 2006) p. 66.
[34] 德國藝術史學者Werner Busch(1944~)的研究顯示,施萊爾馬赫的「藝術宗教性」概念吸引著佛烈德利希。詳見Werner Busch: Caspar David Friedrich. Ästhetik und Religion (München: C.H.Beck, 2003) p. 161.
[35] (⋯⋯)die wahren Beschauer des Ewigen waren immer ruhig Seelen, entweder allein mit sich und dem Unendlichen oder, wenn sie sich umsahen, jedem, der das große Wort nur verstand, sein eigne Art gern vergönnend. 摘錄自: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Über die Religion. Reden an die Gebildeten unter ihren Verächtern (Reclam, Stuttgart, 2007) p. 44;中文譯文:「(⋯⋯)真正觀看永恆的人永遠都有寧靜的心靈,或者僅僅同自身和無限相望,或者當他們環視自我時,每次都只能滿足於以他特有的方式領悟大道」參照:施萊爾馬赫著,鄧安慶譯:《論宗教:對藐視宗教的有教養者講話》(香港:道風出版,2009)頁41。
[36] Werner Busch: Caspar David Friedrich. Ästhetik und Religion (München: C.H.Beck, 2003) p. 64.
[37] Ibid., p. 68.
[38] 1980年的專題:「信仰的符號-前衛的精神:在二十世紀的藝術裡的宗教性超驗」( Zeichen des Glaubens – Geist der Avantgarde. Religiöse Tendenzen in der Kunst des 20. Jahrhunderts, Schloß Charlottenburg, Berlin) ;1990年的專題:「當代永恆:在我們的時代藝術中顯現的超驗足跡」(GegenwartEwigkeit: Spuren des Transzendenten in der Kunst unserer Zeit)。參照Rainer Beck, Rainer Volp, Gisela Schmirber(Hg.): Die Kunst und die Kirchen. Der Streit um die Bilder heute. (Brückmann, 1984) p. 174.
參考資料(選)
Werner Busch: Caspar David Friedrich. Ästhetik und Religion, München: C.H.Beck, 2003.
Hans-Eckehard Bahr: Theologische Untersuchung der Kunst, Poiesis, München und Hamburg: Siebenstern Taschenbuch Verlag, 1965.
Rainer Beck, Rainer Volp, Gisela Schmirber (Hg.): Die Kunst und die Kirchen. Der Streit um die Bilder heute, Brückmann, 1984.
Kurt Lüthi: Mut zum fraglichen Sein. Wege eines Theologen zu zeitgenössischer Kunst und Literatur, Hora Verlag, 1996.
Horst Schwebel: Die Kunst und das Christentum: Geschichte eines Konflikts, München: C.H.Beck, 2002.
Herrmann Zschoche (Hg.) : Caspar David Friedrich. Die Briefe, Hamburg: Conference Point Verlag, 2006.
James Breslin著,張心龍、冷步梅譯:《羅斯科傳》,遠流:1997。
James Elkins:《繪畫與眼淚》,左岸:2004。
Peter Gay著,梁永安譯,《現代主義:異端的誘惑》,立緒:2008。
羅頌恩著:《睜開眼的祈禱》,宇宙光:2022。